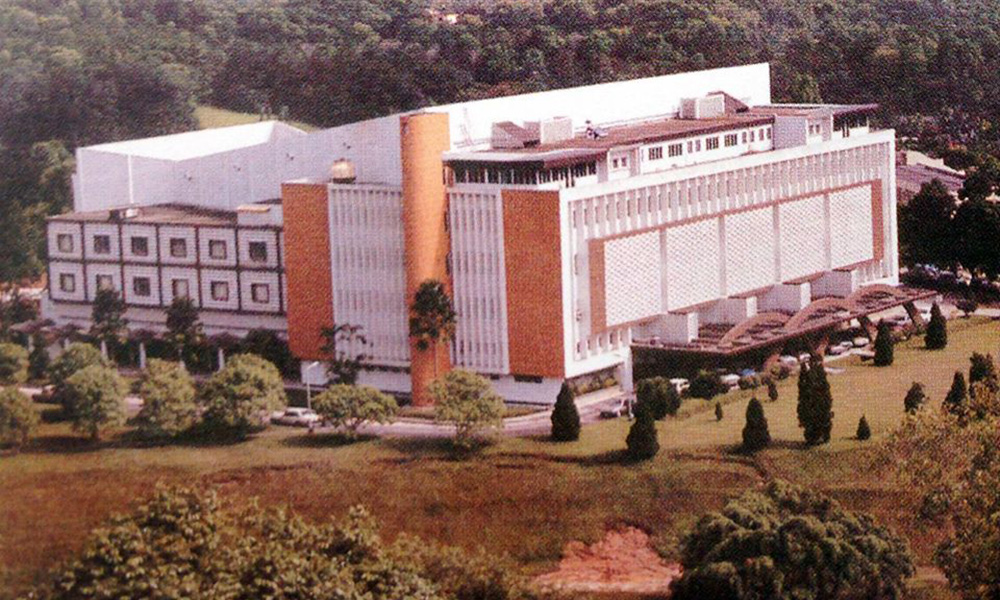南大四十年祭
【当今特约】
2020年初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迅速蔓延,全球一片哀鸿遍野,似乎遥应了庚子必乱之谶言。对华文教育来说,今年也应是忏悔之年。回首四十年前,南洋大学惨遭强行关闭,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历史伤口。逢此险厄凶岁,抚今思昔,怆然莫名,感系愈深。
四十年不长不短,人世间换了一回。1980年南大被鲸吞后没几年,岛国最后一间华文小学也被关闭,社会改造大工程进入了收官阶段。从九十年代“伪西方社会”(李光耀语)的成形,到二十一世纪初英语成为大部分华裔小孩的母语,也不过是一代人的光影,却翻转了南洋原有的精神面貌。
南洋大学,这个改造工程中最难以攻克的关卡,李光耀晚年回忆起来,还无不得意地说他可是“花了十六年才解决”,掩不住那处心积虑之心迹,却也折射出他内心一个巨大的阴影。
顶端大图:1955年南大创办之时,南大牌坊作为南大的标志和正门入口处,牌坊写着“1955南洋大学”。“南洋大学”这几个字是当时国际书法家于右任的墨宝。(图文取自面子书“南洋大学”专页。)
官方给南大下判三“罪状”
历史从来都由胜利者所书写。从国家机器的强暴,到钦定历史的书写、主流意识的塑造,那个曾经掀起举世狂潮与全民翘盼,矗立起大时代丰碑的南洋大学,早被边缘化为建国史中的小注脚,被捏成面目可憎而定格在史册里。
官方给南大下判的“罪状”,不外乎有三大条:一这是一所华人沙文主义的学府;二是南大与红色共产的关连,三是南大学术水平的低落。其中第一、二条最为严重(此两条实为一体之两面),在冷战时代里简直是罪不可赦。
南大打从立校以来,就不断被责问“究竟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公民还是倾向於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”(李光耀语);不然就被学界论述为“移民社会的产物”、“华侨民族主义”、华人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与错乱等等。
此类主流观点,似乎已成了定论。每念及此,未免惶恐。南大不死,只是调零。我们已输了南大,不能再输掉南大精神,更不能输在最后的历史防线上。藉此四十周年之际,让我们好好地把南大史重读一遍,本文且先重审所谓的第一条罪状吧。
建国堂。南洋大学已被拆除的大楼之一。
吾人之故乡:陈六使倡设大学
一部南大史当从何说起?1950年5月,一代侨领陈嘉庚决定北归中原,贡献祖国,象征了侨民时代的逐步谢幕。当时在码头为他送行的接班人陈六使,以及他身后数以百万计的各地华人,却决意要化异乡为故乡。但是他们该以什么身姿留守在南洋?
四个月后,陈六使给出了答案。1950年9月,六使伯以高瞻远瞩之姿,倡议华人应率先主动创建一所大学:
“自第二次大战后,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。既有此一新见解,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。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,中学生之多,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新加坡不可,愿各位贤达共促成之。”(引自雷澥《南大春秋》,页22)
据此而论,南大乃因应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——为“吾人之故乡”马来(西)亚此大因缘也。“既有此一新见解”一语,寓示了一种新认知的产生,宣示了身分认同之转变。每读史至此,莫不掩卷长思,继而废书而叹:解读南大史之线索尽在此矣。可惜后人大多错读了南大,不然便是存心要扭曲南大。
1950年首议未引起关注,至1953年1月16日,独立自治形势愈形逼近,时机不再待人矣。于是陈六使在主持新加坡福建会馆联席会议上,毅然再次高呼 ——马华社会当以自身人力与物力创办一所“马华大学”。
没想到此次登高一呼,如平地一声雷,万山响应,大地震动;又如星火之燎原,一发不可收拾,全马迅速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“南大运动”,实为前所未有。

陈嘉庚与陈六使(左)
当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锡九,亦随即作出积极响应:
“目前居住本地之华人,大多数已认本地为家乡,在本地创办一间大学培育子弟,为本地服务,实为一件有价值的工作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23)
所举创办大学之理由,同样是因为南洋华人“已认本地为家乡”了,与陈六使之说相发明。紧接十天后(1953年1月26日),《南洋商报》刊发了一篇重要的社论《我们对马来亚的正确立场》,揭出了这场南大运动的时代意义:
“今日华人……视此为第一故乡了;过去为中国兴学,今日转为马来亚兴学了。我们愿以马来亚为国家,“使河如带,泰山若砺,国永宁,爰及苗裔”。于是,华人领袖倡办马华大学,这是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。”

南大精神:时代的民族精神
过去为中国兴学,今日转为马来亚兴学,因为这里才是真正的第一故乡——创办大学最大、最高之意义全在此矣。这是我全体华人“对马来亚的正确立场”,也是“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”。
还可注意的,大学最初名称叫“马华大学”(后因殖民政府干预而改为“南洋大学”)。马华者,马来(西)亚华人之谓也,乃是一种新身分名号之确立。此篇社论独具慧眼,贯串起大学创建与认同转变的内在理路,点透出南大运动背后巨大的历史意涵。
5月18日商报再发一社论《南大精神——应具愚公移山志愿》,更是先时地拈出“南大精神”四个字。一所大学倡议不及半年,校舍尚未绘图,竟然先凝萃出一股惊心动魂的精神来,实为人类史上所少见。若不是汇聚了整个民族的人格力量以及历史大潮的殷切吁求,哪能如此快速结晶成一条传神而动人的时代标语?
南大使命:沟通东西文化、发展马来亚文化
1953年4月7日,创校筹委会发布《创立南洋大学宣言》,向天下昭告创校的四大理由与两大特质,深切反映了南洋华人于此时此地的处境、抉择与志愿。
四大理由中的两大点:“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”与“为适应人口上之需要”,正是一种以国民身分来发言的立场与措辞。
就如陈九锡所言的,为本地子弟服务才是最有价值的工作!至于南大两大特质,也就是她的两大使命:“沟通东西文化”与“发展马来亚文化”。对于后者,宣言这样说:
“马来亚为华巫印等民族和衷共济之邦,各民族间接触频繁,精神联系,感情融洽。南洋大学之特质在研究各民族文化,吸取各民族之菁华,使马来亚文化有辉煌之成就。因此马来亚各民族之地理历史物产经济语文等科目,均为南大研究之中心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37)
明明白白地宣示,创设南洋大学的最高宗旨,就是为了研究、创造与发扬马来亚文化。据此,南大创校之宣言,实无异于华人落地生根之宣言。
1954年8月“世界青年大会”在新加坡举行,陈六使以东道主身分宴请各国嘉宾,他在致词中言及即将落成的南大:
“南洋大学的使命是伟大的,它配合新马其它民族,各发扬其固有文化,从而融合以求产生一种奇光异彩之新兴文化,为人类文化史开一新页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67)
同样强调了南大的使命,是要发扬新马各族固有之文化,以期融合成一种新兴的马来亚文化。可见这实在是陈六使一贯的信念,也即是南大自始的立校精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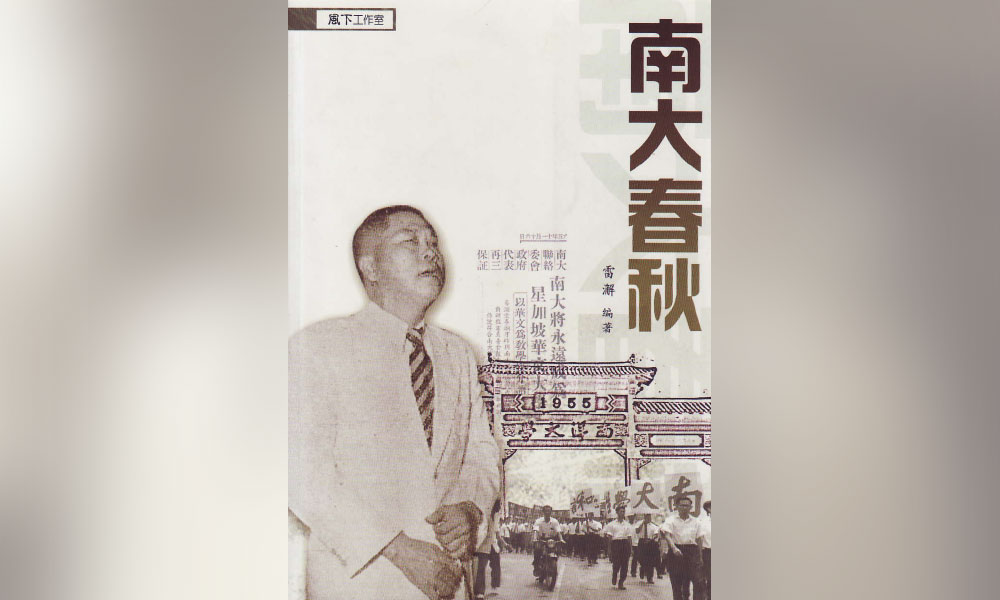
南大:追寻新家园的精神表征
再看,曾参与过南大初期科系设计的南洋学巨子许云樵,也于1953年12年撰文指出,南大首先必须具备“本位文化的中心”之特质,否则既使办得再怎么好,“也已失掉了南洋大学之为南洋大学的意义了”。这是因为:
“我们已非作客时代,我们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部份,我们当负起这使命来,而南洋大学当然是这场文化运动的中心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268)
依许氏揭示之意,南洋大学实为南洋华人追寻新家园的精神表征,也将成为倡导这场南洋新文化运动以及建立“本位文化”的中心点。此精辟表述,适可与创校宣言、商报社论等相互映发,相得而益彰。
由此可见,当时的有识之士,莫不视南大之创建,为一场伟大的南洋华族欲昂首立命于斯土的新民运动。
凡欲认识南大的历史蕴意者,当由此义来观察之;欲评论南大之作为与成就者,亦当从“发展马来亚文化”来衡估之;此“发展马来亚文化”一义,还可从其建校规划、科系设置、校园文化、学术成果等具体考核之。否则动辄据“华人”“华文”一端而随意扣上种族沙文主义大帽,岂此有失公道,简直是谬以千里,不知南大为何物了。
南大:真正的国民大学
南大于1956年3月正式开课,时任首席部长马绍尔专函道贺,赞赏南大将是“各族合作及马来亚忠诚之明灯”。1958年 3月30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大典,吸引了十万人潮莅临观访,包括各国政要与嘉宾。会场内是挤得水泄不通,场外则车龙堵塞十多公里,交通全面瘫痪,大家只好步行长途赶去观礼,盛况为新马开埠以来所未有。
陈六使在最后压轴的演讲上,激昂而自豪地高呼:
“本人屡屡大胆声言:南洋大学乃新嘉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。本大学乃此时此地华人大众于纳税义务之余,赠予新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之崇高礼物,将为二邦分负高等教育责任,藉以教育其公民,俾各尽所能参与建国之大业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77)
陈六使以高亢声调,极力陈言南大就是一所“真正的国民大学”;是华族为了教育马来亚公民,为了“参与建国大业”,而特别奉献给新马的建国大礼。这番振奋人心的爱国表白,有在场十万国内外嘉宾可作证。
青年李光耀当天也应有在场,却不知是否聆听了进去?不过现场的澎拜情怀与盛大民气,想必是将他震撼住了,让他再次见识了“华校生的世界”。待次年(1959)他一上台执政,就迫不及待地筹谋“解决南大”的长期计划了。
为什么陈六使要“屡屡大胆声明”,南大是“真正的国民大学”?当时新马仅有二所大学,另一所为马来亚大学(后改名为新加坡大学,后再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),乃由殖民宗主所开办,旨在培养少数社会精英,是一所以西方文化霸权为中心的“殖民地大学”,这是当时人的普遍观感与评价。
相较之下,南大则是一所下接地气的本土学府。她由国民因应建国之需要而自主开办,以教育国民子弟为己任,深具国民性与民间性。早期的南大学生,无不映现了这样的气息。
1958年4月23日南大学生会宣告成立,赤胆誓言“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”,这里的“祖国”是脚下的马来亚,而不是远方的中国。这便是创立南大本有之义,也是南大生应有之义。且看《南洋大学学生会成立宣言》曰:
“南大学生会将协助南大发展成为星马各族青年研究学术的高等学府,及各族文化交流的领域。……把学生的力量汇合到建设国家工作的洪流里去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86)
可见南大学生会的宗旨,一是促进各族文化交流,二是要参与到国家建设的洪流去,这与陈六使所说的“参与建国大业”理念,何其相应契合呀。易言之,南大运动不仅彰显了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意义,更体现出华人欲当家做主之志愿,也就是要主动积极参与到建国大业去。
一部南大史,实可从华人参与独立建国的历史来解读。这其实是马新华文教育的特有之义,而为世界其它地区华教之所无。
南大:本土文化的实践场域
华文教育扎根南洋百余年,安家兴邦是必然之结果,南大则为结穴之所在。早年南大校园俨然是本土文化的实践场域,各类学生活动、学术研究、文娱创作演绎等,多围绕本土因素而创发、改良与融合。这里甚至是马新最早推动国语学习的基地。
曾任教于南大的国际著名作家韩素英,当年就如此称赞说:“南大学生实在是幸运,能说人民的语言,且能了解人民的问题,而且又积极地学习国语。”1960年韩素音在一场演讲上,再次赞赏台下的南大生说:
“南大已经是马来亚文化的一主要部分。学生们,马来亚文化已在你们的手中,你们有责任将它丰富与美化起来!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281-282)
从1956年开办到1960年,也不过是四、五年时间,南大已建立起一个“能说人民的语言,了解人民的问题”的本土场域,化成了马来亚文化的一部分了,实不辜负于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中心(许云樵语)。
套用人文学界流行的“去殖民化”理论,南大的创建显示了另一层历史意义,那就是她有意识地推动和建构本土文化主体性(亦许云樵所言之“本位文化”)。从批判殖民文化霸权、倡议民族自决,到追寻自我价值、创造本土语言等等,都是预先为后殖民社会的到来作准备,实为马新“去殖民化”历程中的先行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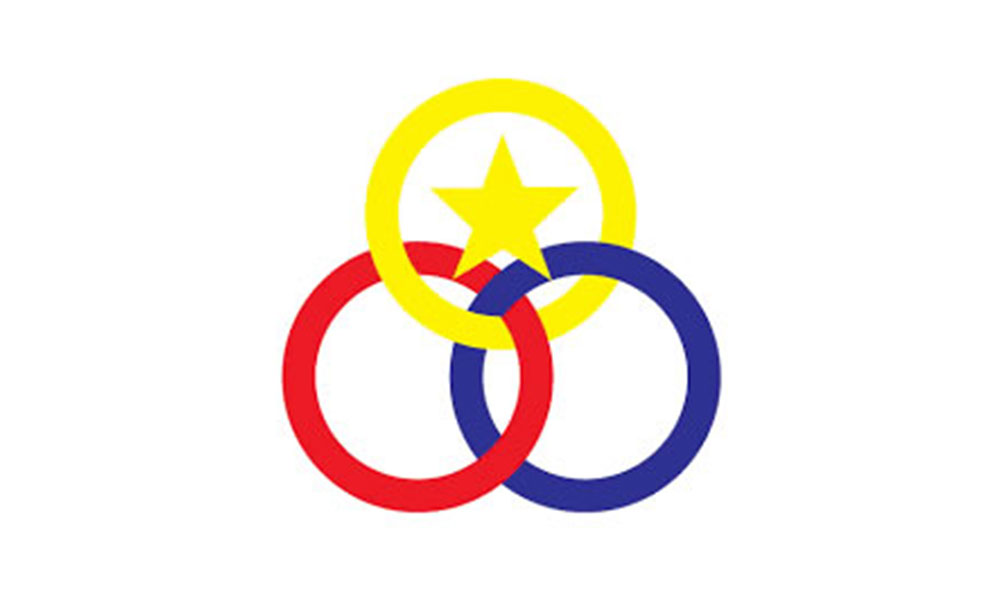
南大的校徽是一座星和黄、蓝、红三道光圈所组成的图案,这图案的总结构象征了交流,相辉与团结。(参见《南洋大学创校史》“南洋大学校徽释义”一文。图文取自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)
“去殖民化”的超越时代
换言之,官方与舆论每好指责南大“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”,或许那恰恰是因为南大“去殖民化”的超越时代,而无法被残抱殖民主义者所理解和所接受。看晚年李光耀一再对南大的评击:
“(南大)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,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。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,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,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。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。”(《新加坡双语之路》,页70)
在当权者的眼中,南大先天就注定要失败,因为她要在“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了栽培中国的果树”。对此刻板印象或莫须有之论,陈六使早在1961年南大第二届毕业典礼演讲上回应过:
“南大的办理方针,是实事求是,是真正效忠国家,是真正马来亚化。所以本人一再宣布,南大是星马一间国民大学。华、英、巫、这几种语文,可以说使星马两邦的文化土壤;南大耕耘的是星马两邦的文化土壤,吸收的是赤道地带的雨水与阳光,当然种出来的果子,只会是榴梿或红毛丹,不会是荔枝或龙眼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151)
看陈六使苦口婆心“一再宣布”,南大是一所深深植根于在地的国民大学,是真正的马来亚化,是热爱效忠国家的。这一次,他还做了个有趣比喻,赤道产生的只能是榴梿与红毛丹,而不会是北国的荔枝与龙眼。我们相信,如果能给予南大足够的岁月来酝酿,这些热带果实终将会“丰富与美化起来”(韩素音语),成长成赤道上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。
不见容于殖民者及其继承者
然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,华文教育绝不见容于殖民当权者及其继承者。看那所谓的“在东南亚土壤上栽培中国果树”云云,不正也应合了当年盛行将东南亚华人视作中国第五纵队的论调么?再看1963年4月7日《星洲日报》社论中所言:
“一年多以来,社会上的流行风气,好像正有人在设法制造一种印象,令人以为华文教育是一切捣乱破坏的万恶之源!”
这便是当时的社会氛围,思之令人惶恐!南大作为华教最高学府,无疑便是这个“万恶之源”的总源头了,结局早可预知。就在同年的2月2日,李光耀发动了“冷藏行动”大逮捕,将左翼势力肃清殆尽,并派军警闯入南大校园逮捕数十名学生,查封了七种学生刊物。然后同年9月16日,新加坡高调地加入马来西亚计划,还打出了“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”的漂亮口号。
好一个高官可以任意放火,建设马来亚的南大却不准点灯。仅六天后9月22日,新加坡州政府就以迅雷之速,剥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;接着9月26日军警再度摸黑闯入神圣校园,殴打逮捕手无寸铁的学子,气得同学们质问这难道是“马来西亚给南大同学带来的礼物”?
年底12月9日,李光耀在立法议会中宣称,如果再不给予制止,南洋大学将会变成一所“延安大学”;随即次年中央政府就发布了《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》,再次年《王赓武报告书》紧接出台,……往下的故事不必细表了。总之,南大从此进入一个“失掉了南洋大学之为南洋大学的意义”(借许云樵语)的收编过程了,直到1980年被腰斩为止。

结语:且待红毛丹熟满青山
南洋果树最终没能丰富美化起来,只留下了千古之遗恨。此中有太多的悬疑,亦有多层的蕴意,自有史家学者去评述。这里权且援引1956年南大文学院院长张天泽的一席话,来作为本文结语:
“余以为南洋大学之缔造,实海外同胞精神命脉之所寄;吾族在海外未来之荣枯消长,胥可以南洋大学之兴衰成毁卜之。”(引自《南大春秋》,页310)
四十年来家国,兴败谁与说?且待红毛丹熟满青山,果王飘香之季,掬一缕赤道的阳光,洒净以热带雨水,以奠祭南大在天之英灵。呜呼。
徐威雄,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,林连玉纪念馆馆长。
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《当今大马》立场。
每月12.50令吉
- 无限畅读全站內容
- 参与评论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
- 与亲友分享《当今大马》付费内容
- 可扣税